|
一个作家在讲解作品时是可以长驱直入的,这对他有天然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他们显然比学者幸运和幸福很多。2017年12月17日,受凤凰网文化邀请,阎连科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给读者们带来了一堂文本细读课。为什么要讲博尔赫斯?这个理由却或许是阎连科的无奈甚至哀求,阎连科说在我们既拒绝向东也不能向西的年代,像博尔赫斯一样写作或许是一次策略性的迂回。当我们已无力像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写出生存的苦难,对于文本空间本身的可能性开拓或许是抵制那些撒娇卖萌文学的一张药方。 “苦咖啡文学的写法是从二十世纪向19世纪回撤”,“《南方》里的每一句话都在带动情节的前进”……这不愧是真正的文学课堂,讨论的是具体的文学技巧和现象,是以作品现身说法的文学史。脱离理论和学术的包袱,这或许就是作家胜于学院派的地方。 “苦咖啡文学”是阎连科对当下中国文坛风向的判断。“咖啡再苦也是咖啡,有一点冷酷,有一点人性,到最后一定是甜美。我也不是说这种文学不好,但是它现在太多了。”毫无疑问,阎连科对待文学的姿态里有激情和崇高,就如他自己所言,有“老一代作家”对“民族”、“命运”、“兴亡”这些文学阐释辉煌主题的无比尊敬和渴望。然而在这个“佛系”当道的年代,文学展示生存的困境与苦难,这是否是一个已经远去的使命呢?亦或是生存困境的本身已经发生了转移?  阎连科 以下为演讲实录 1. 十年前我到阿根廷的玫瑰公墓去找博尔赫斯的墓碑,我们找来找去找不到博尔赫斯,我问导游:“博尔赫斯在阿根廷难道就没有一点名声吗?”我想其实博尔赫斯是非常不希望我们这样大庭广众去讲他的,他在阿根廷几乎真的是沉寂在深层的故事中间的,甚至只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放着。第二次返回到玫瑰公墓的时候我找到了博尔赫斯小小的墓碑,是我们这个纸张的一半这么大。 我想不论是博尔赫斯还是他的夫人都不会想到博尔赫斯在中国,尤其在法国在欧美有这么大的影响。我想博尔赫斯是一个冷文学,冷文学我们讲起来可能更加有趣,也更难听一些,更不热闹一点,但是我们讲起《南方》来,会发现这个人的写作至少和我们中国作家确实是不一样的。 我为什么要选讲博尔赫斯这个话题,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上午忽然想到:今天,中国文坛到了一个巨大的被误导误读的时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今天都非常清楚,社会要求作家和文学必须承担起太阳、月亮的功能,而文学恰恰又没有这个功能。文学是非常寒冷的,作家也是非常寂静的,他只是希望在太阳下边晒晒暖,在月光下边交谈交谈,散散步而已。 对文学这个功能的要求是一个回归,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文学都是这样的,但是在有这样功能的时候,我们从来没写出像博尔赫斯这么好的小说来。当我们赋予文学这么大功能的时候,我们发现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是什么样的文学呢?——颂政文学。《人民的名义》,它非常清晰的就是这种文学,它是不是文学我们且不去讨论,有多好我们不去讨论,但这种文学以后会越来越多,小说、诗歌、散文会回到我们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乃至于回到文革时的样子。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这个东西我想没有什么好不好,习主席要求我们要歌颂党,歌颂中国,歌颂人民,歌颂英雄,在这四个歌颂的基础上,这个文学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但需要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年代不再是那个年代,作家不再是那个时代的作家了。 为什么说我们再也写不出《青春之歌》,写不出《烈火金钢》,写不出《野火春风斗古城》,写不出“三红一创”这样的作品了?因为今天的作家和那时候是完全不同的,那时候作家对某一种政治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他写出这样的作品是非常正常的。 但今天我不太相信,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作家他们内心对某一种信仰能够像当年那些作家那样坚定,当一个人内心信仰发生问题,再去写那样的文学是会打折扣的,我们真的是再也写不出那个时代的作品了。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我们可以等三年、等五年、等十年,也一定写不出《青春之歌》那么好的革命小说来。 这次我想不是这种文学好不好,而是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完成了,我们再也回不到他们那个对共产主义那么信任,对解放全中国的信心丝毫没有掺假的年代了。在那种信仰下,他们写出了今天来看仍然被推荐,被叫好,仍然被教育部门推广为青少年必读的作品来。今天我们必须写出这种文学,又写不出经典级的作品,我想每一个作家都是非常困惑非常焦虑的。  《青春之歌》,杨沫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在今天我们要求一个作家要像太阳像月亮那样发光的时候,我们写不出这种文学来,那我们能写出什么样的文学来?我想这第二种文学其实已经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了,我想了半天怎么给它命名?我想就是——苦咖啡文学。 今天咖啡馆文学非常盛行,并不是说在咖啡馆写作就叫咖啡馆文学,而是这种文学的风格:温暖中有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一点伤痛的文学,这是我们今天的作家整体在追求的一个文学局限。青年作家也好,中年作家也好,乃至于那些一片叫好声的耳熟能详的老作家,今天也到处走街串巷去吆喝地、卖地,恰恰就是这种苦咖啡的文学。但是无论它有多苦它也是咖啡,这种文学今天特别的流行。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苦咖啡文学,我经常说是因为今天确实要承认鲁迅从我们的写作中基本上彻底退场了,鲁迅退场的时候我们其他作家既走不到那种颂政文学,又走不到鲁迅这个时代,那能产生什么?就是像苦咖啡一样的小说。不管你是在家写的,在火车上写的、飞机上写的,哪怕你苦心经营睡到半夜重新起床写的也是一个咖啡文学。 这种话在今天说不是特别合适,但我们看我们今天特别是那些卖三万册、五万册或者一片叫好声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小说根本上就是既带着咖啡的甜味,也带着咖啡的苦味,带着咖啡的一切可能性,温暖的、甜美的但是也是苦涩的,有一点点的人性的存在,或者说人性占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种人性也一定是甜美和温暖的。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无法把这种文学以80后、90后、60后、70后去分它,人民大学的杨庆祥老师曾经说过一个今天的文学是“新伤痕”文学,我觉得那是对文学过高的估计,“新伤痕”文学是非常少的,我觉得这个苦咖啡文学恰恰是普遍流行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苦咖啡文学,我们不要去谈特别具体的作品,你随便去买一种,拿回来看它一定是这样的,有个前提是温暖的,一定也有苦涩,它有寒冷但一定很人性的,人性又是非常温暖的,今天这种小说读者喜欢,批评家喜欢,文学史也非常的喜欢,这是我们文学强大的一个传统。 今天鲁迅退场的时候,苦咖啡文学又产生了。我们文学中已经没有任何苦难也没有任何人生的经历问题,所有的经历都是在咖啡馆中间产生的,痛苦我们可以到咖啡馆去谈,苦难也可以到咖啡馆去谈,即便人生的生生死死也可以在咖啡馆中去谈,当我们的任何的苦难、经历、困境,都可以约上一个朋友到咖啡馆去谈的时候,其实这个苦难这个人类的境遇的困境已经被我们消解了,它已经不是必须生生死死要在悬崖上跳下去才能喊出的“啊”的一声,它一定是有强烈的咖啡的味道。 我们可以坐在这儿谈文学,谈苦难,谈失恋,谈情感,谈婚姻,一切可以进入咖啡馆谈的东西,已经是被我们消解掉的,已经不再是我们说的鲁迅,沈从文,甚至也不是张爱玲的了。  沈从文 对于这种文学的命名由批评家去说,但大体上一定是这样一个情况,咖啡馆是什么风格,这个小说就是什么风格,咖啡馆是什么氛围这个小说就是什么氛围,咖啡馆的语言有多好这个小说语言有多好,咖啡馆有多么苦难,这个小说就有多么苦难,如果咖啡馆充满着温情充满着神秘,充满着东西方文化的结合的时候,这种小说也同样充满着东西方那种文化文学的结合。 但是我们仔细去想,除了我刚才说的社会原因和国家对作家要求的原因,这种文学之所以流行,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就是这个小说我们不能说它好或者不好,一种新的文学经典的转移,导致了这种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我们不能简单说它是因为鲁迅的退场而产生,也不能说是因为要求作家承担起巨大的无法承担的责任而产生,也不能说这是因为我们写不出来或不愿意写颂政文学而产生,或者说是因为我们对某种信仰的怀疑而产生。 这种小说它是非常有根源的,最近十年来在中国比较盛行的西方的经典文学,可以说是卡佛的小说、门罗的小说,弗兰岑的小说,村上春树的小说,村上实际上比较早,把这一类已经成为经典的小说放在一块儿去比较我们会非常清晰的发现一个问题:门罗也好,卡佛也好,村上春树也好,弗兰岑也好这些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自由》也好,卡佛小说集《大教堂》也好,村上春树所有的小说也好,也包括门罗的《逃离》等等这些经典作品,这一类作家全部都有一个特点:在写作的内容上,在写作的人物上已经在从社会历史向家庭转移,基本不是家庭也是微小的人群,是那么两三个人、四五个人、五六个人。 这些作家在西方也非常有影响,但不会像我们中国的作家读者一样对他们那么崇拜。这些经典有个特点,就是写作充满着苦咖啡的味道,和我们今天所处的现实写作几乎是一脉相承的。不是说这种小说好不好,而是它的写作内容发生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转移,再也没有《战争与和平》那么宏大的历史,那么大的苦难;也不会有巴尔扎克那样的对整个社会的描述和关照,对整个民族的关心;当然也不会再出现像卡夫卡小说中对个体的人的深刻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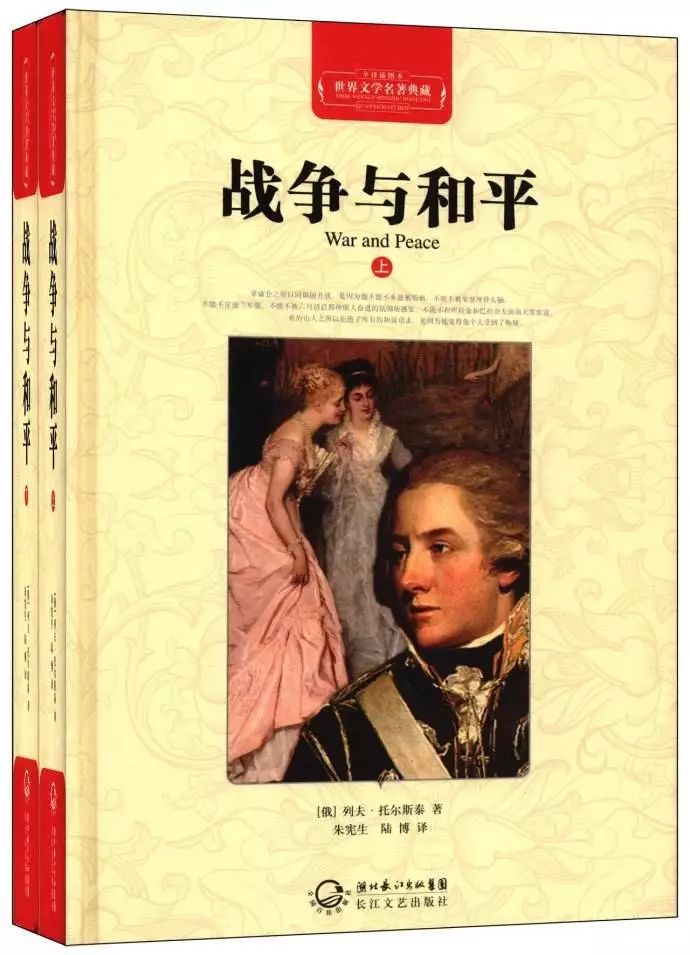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这些文学好像也写的是个体的人,但是这里个体的人一定不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了。对于这种转移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性,而这个共性恰恰和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现实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特别需要对这些人群的关心,一个微小人群,家庭、小伤感、小温暖、小挫伤、小确幸这些东西来,恰恰是这种情况导致了这种文学在中国的盛行。 但是这些作品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写作的方法上如出一辙,就是说彻底的从二十世纪向后撤,在写作的方法上从二十世纪文学后撤,再也不去做那些文学形式上的带有风险性的探索和创造,他们对读者的热爱远远超出了二十世纪那些作家。二十世纪的作家会说我不为读者所写,我只为我自己写,他们确实也非常关照读者,但关照读者也不是金庸那样关照,是另外一种。 这就是从二十世纪的写作方法向后撤的一个可能,但回头来说它绝也没有回到十九世纪小说“故事”、“人物”那套系统中去。它在写作方法上是在二十世纪和十九世纪之间来回摆动的,所有小说的方法用的是十九世纪靠前一点,二十世纪靠后一点的。村上春树是最典型的,村上春树的小说你说他传统吗?他一点都不传统。他要比十九世纪的小说先锋的多,有创造性的多,但你说他创造性多,和二十世纪那些伟大的具有创造性的作家简直不能同日而语。 这是一个纵向的比较。门罗、卡佛、弗兰岑在写作方法上从二十世纪后撤而在十九世纪又向前,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写出了我们今天在座的包括我在内也非常喜欢的,所谓的“苦咖啡文学”这样一个东西来。这是他们写作的内容和方法。  村上春树 我们四百年、五百年、两千年的文学经典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发生了转移。在我们当下的写作中间,我们每天嘴上都在谈陀思妥耶夫斯基,谈托尔斯泰,谈卡夫卡,谈博尔赫斯,但都是在嘴上而已,而不在文学中间。真正被借鉴的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作家,但是我们谈论卡夫卡,谈论博尔赫斯,谈论马尔克斯,谈论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文学,也包括鲁迅。 鲁迅今天完全停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嘴上,但纸张上是基本消失的。这样说有点绝对,但事实上就这样。而我刚才谈到这些作家,卡佛,村上,他不像鲁迅那样被我们挂在嘴上,但确实都出现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间。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们说的是鲁迅、托尔斯泰、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我们写的是村上春树,是卡佛,是弗兰森。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们说的是另外一些伟大的人,但我们写的是另外一条河流另外一种文学,这是我们文学今天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你去谈论文学,每一个人谈论的都是上面说的最伟大的作家,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经典,但写的文学和那些基本没什么关系。小说形式上当代作家说的都是要创作要创造,但实践上恰恰是在后撤。 以卡佛为例,以另外一个美国作家写《好人难寻》的奥康纳为例,他俩同样是美国作家,几乎又是同代人,几乎又同时走进中国。我个人认为,奥康纳小说写的那么好,我个人以为远远比卡佛好得多,无论是她的叙述技巧还是对人性的挖掘,远远比《大教堂》、比卡佛好得多。不管卡佛是用极简主义也好,这个主义也好那个主义,我们仔细去分析去看,奥康纳恰恰在展现人性这一点上,是卡佛所不能及的。但今天为什么卡佛能这么的成功,让所有的作家都去学他;而奥康纳,不能说完全不被接受,只是被极少数人关注和阅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奥康纳 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就发现卡佛的小说就是我们说的苦咖啡的味道,奥康纳恰恰在人性在生命这一点上写尽了人类的邪、恶、丑。二十世纪下半叶再也没有一个作家在写人性的邪恶丑上能够超过奥康纳,再也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奥康纳那样把邪恶丑散发在小说中间散发在那么的滴水不漏,蛛丝马迹一点都不留痕迹,而且读起来让我们不会觉得这个人写的就是脏就是丑。 我们从奥康纳的小说中丝毫感受不到所谓的脏的丑的乱的,但是我们仔细去分析她作品的人物就发现她写尽了邪恶丑。但是卡佛恰恰在这点上和她相反,我们看卡佛也写了非常多的人性,比如《大教堂》,但这种人性却充满着咖啡馆的温暖的气息,充满着我们能够接受的能够想像的,甚至在我们生活中能够发生的情节。就这两个作家被接受的情况比较,我们非常清楚为什么某一种文学被拒之门外,而另一种文学被接受下来,这就是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咖啡馆的时代,文学进入了咖啡馆文学的时代。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情况产生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最年轻的作家中间,在80后、90后作家中间,他们已经对经典进行转移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可怕的,他不再认为卡夫卡是伟大的,也不再认为托尔斯泰伟大,也不再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所有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家在他们这里是几乎不存在的。这代作家写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代作家已经成功的把经典转移到了另外一批经典作家中间。我经常说,如果有一天门罗也获奖了,村上春树也获奖了,整个世界文学对经典的转移就已经悄然完成了,那不是谁的成功谁的失败,而真的是我们长期崇敬的伟大作品的一次灾难。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 四年前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家讨论村上春树,村上春树获得了日本所有作家的赞同,一片的掌声,所有的文章都是赞扬的,唯有我最不合时宜的去讲了讲,我说村上春树是非常伟大的,他的书畅销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们到挪威去,挪威的同一个出版社说阎连科老师你的书卖的非常好,我说卖了多少?他说卖了五千册,然后说村上这次书卖的不太好,我说卖了多少?他说卖了五万册,我说卖的好是多少?卖的好是二十二万册,挪威只有几百万人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卖的不太好卖了五万册,卖的比较好卖了五千册。我不是说村上春树写的不好,就个人阅读来说我们从村上春树的小说中间看不到日本人今天的生存的状况,一个伟大的作家,一部伟大的作家如果不给读者和批评家展示他本民族人群最艰难的生存境遇和生存困境,这个作家的伟大是值得怀疑的。 村上春树卖的非常好,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包括横光利一、芥川龙之介等等这一大批作家加在一块儿卖的都没有村上卖的多。但是我说,从你们日本上一代作家每一个人的作品里,我都能看到日本这个民族的生存困境,但是从村上春树小说中间我看不到这一点。村上春树比上一代作家卖得好的多,但是赢得的尊重的目光却少得多。  川端康成 今天我们也恰恰会遇到这个情况,当我们看到我们当下的小说全部都是苦咖啡文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群在某一阶段某种情况下遇到的小困难小波折,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生存困境在哪里。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全都是鲁迅,我说这个文学冷酷无情,一点意义都没有,一定是要有沈从文、张爱玲等等等等作家的。如果我们的文学全部都是这种苦咖啡文学,都是门罗都是卡佛而不存在鲁迅,我们的社会问题可能显得更大。 问题就在这里,我今天从我们年轻作家中间再也找不到,不是说他对整个民族关心不关心,也不是说他对国家关心不关心,鲁迅的小说我们也感觉不到他一定对中华民族多关心。但是有一点就是从今天这一代作家中,我们感受不到你所处的人群,你所处的时代,你遇到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人的生存境遇是什么。 我今天这么说有点得罪大家,也得罪我们的同学们,但我一直在说80后的作家亟需要你要给我们提供一个范本,讲讲80、90后的孩子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难是什么。我没有从一个我们80后作家的小说中读到这个东西。他们的文字要比上一代作家写得好得多,比我写的好得多,他们读过的书也比我多得多,他们的聪明智慧情商也比我高得多,50后作家的语言和80后作家比较,那真是小巫见大巫的。 每一个80后作家拿出来都是新概念作文里边的第一名,在我们那时候写一篇作文是要查十次、二十次字典的,他们能迅速就写出新概念的一等奖,这种语言超出我们的想像,但是当他们写一部小说、两部小说、三部小说,我们仍然找不到这一代人在那个小说中间表达出你同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时候,我对这种小说是非常怀疑的,我怀疑当有一天你不去敲锣打鼓走街串巷卖作品的时候,这些小说是不是就悄无生息的消失掉了?我想这才是我们已经三十岁四十岁的80后,或者非常年轻90后作家应该去想的。 你不要想你今天的小说如何,而是想想你三五年以后会如何,十年以后如何。无论你们多么不喜欢余华的《活着》和《第七天》,但我们必须看他的《许三观》和《活着》,那是当年和今天都非常畅销的作品,这是二十多年前的小说,我们也可以想像在二十年以后他们仍然是会有人看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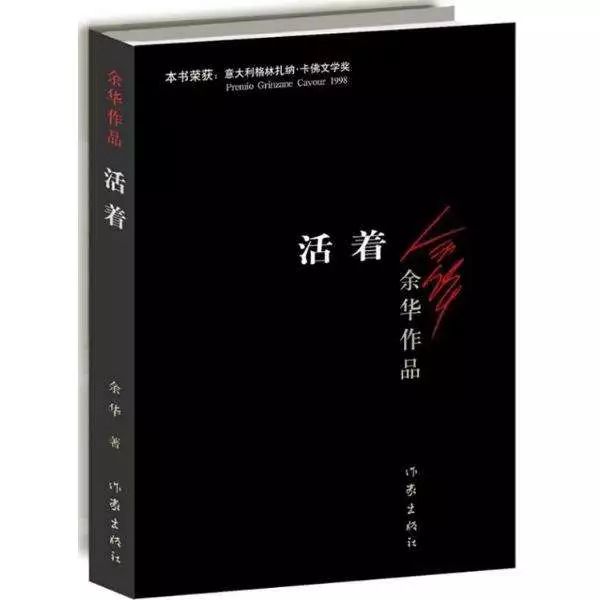 余华《活着》 这件事情我们非常清楚,对于年轻作家来说你一定要去比较,莫言、余华、苏童、格非在他们三十岁的时候写出的是什么样的作品,而你在三十岁的时候写出了什么作品,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和你上一代去比较。你才华比他大得多,你所处的环境比他好得多,你的经历也不比他少,你所经历的人类的情感远远比他丰富的多,无非他是对饥饿和革命比你感受深一点,对爱和被爱,对人的精神困境你比他的经验深刻的多,但是你没有写出小说来,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苦咖啡文学的一种怀疑。 为什么要谈博尔赫斯,恰恰就因为我们说颂政文学我们不去写它,我特别相信我们特别喜欢的作家不会去写《人民的名义》,《人民的名义》非常的伟大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出来的,只有周梅森能写出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但是我们另外一些喜欢的作家,不是你不写,是你写不出来,你没这个能力。那么在这个苦咖啡文学都已经泛滥成灾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像托尔斯泰那样,不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像卡佛那样,我们至少还可以另外一种可以像博尔赫斯这样去写作。 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讲博尔赫斯的理由。我想讲博尔赫斯的文学贡献,其实我们每一个上一代作家包括七十年代每一个人都在谈论他,但是我们从来没想我们为什么喜欢他,我们喜欢他什么。博尔赫斯对世界文学最大的贡献,恰恰是成功的证明了小说可以不写人性,小说甚至可以不写人,小说甚至可以不写生命。 你通读他的小说,难得找到一篇能够像《南方》那样一点一滴的透出人间烟火气息的作品。再看他其他小说,说白了博尔赫斯写作他按的不是人而是按他头脑中的这些东西来写的。没有一个作家在写小说时敢于说这小说根本不写人间烟火,没有一个作家敢于说我的小说根本不塑造人物,即便我们经常说卡夫卡的小说人物是符号化的,但是到了博尔赫斯这里连符号化都没了,几乎就是不写人。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他叙述的方便,非常难得在他的小说中间有《南方》这样一个像我们习惯中的短篇的短篇。  阎连科谈“苦咖啡文学” 我们经常会说,小说是从世俗中来到生命中去的,从十九世纪、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我们都不能逃离这个过程,但是博尔赫斯完全不需要从世俗中来,他根本不喜欢世俗生活。在他的小说中间我们看不到男亲女爱,看不到生老病死,也看不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东西。 我们能说它不是小说吗?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恰恰是因为他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写作的可能性,那些不像小说的小说才是今天我们的文学特别渴望的东西,否则我们就一定会走到卡佛这样一个路子里,这没有什么不好,有这样的作家我们才有在座的非常多的读者,但是每一个作家都这样写作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文学显得非常简单非常的单调。我们其实是希望有非常多的写的不像村上、卡佛的小说出来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伟大的短篇小说中,博尔赫斯完成了这一点,他是唯一一位给我们人类世界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小说的小说,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博尔赫斯的小说,成功的完成了对人性对生命的转移。我们看到世界上那些伟大的作家,当在谈论小说的时候都会说人性,人性,人性,生命,生命,生命。但是博尔赫斯成功的转移了这个小说的主题,他小说不谈这些,不写人物不挖掘人性,不写人的生命过程。他写什么呢?写迷宫、镜子、《一千零一页》、图书馆、语言本身,写某一首长诗中的第一句等等,以《阿莱夫》为例,这是他比较长的一篇,一万多字,全篇说白了就写了一首诗的第一句,也就是阿拉伯字母中的第一个字母,写不出那个字母来,全部小说就讨论这一个问题。 这个作家为什么能让所有的人都去谈论他,乃至于喜欢他,是他给我们成功的提供了小说的另一种可能性:小说完全可以不写生命。现实主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被博尔赫斯推翻掉,说到底博尔赫斯一点不爱人间,他的小说几乎没有人间这个东西。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他给我们开掘了一个小说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不管后来者有没有继承,不管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对他有多么的喜欢,至少有一点,他告诉我们小说在我们的人间烟火之外是有另外一个领域的。 我今天为什么选择谈博尔赫斯,恰恰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对人性进行鲁迅那样的开掘,不能像《战争与和平》那样去认识世界,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想想文学的本身,博尔赫斯所有的热爱就是爱文学本身,他写作不为了任何人就是为了这一个文本。我们看他的短篇小说叙述也好结构也好,我们都无法去谈论他,我已经看了三遍《交叉小径的花园》都没有能力把它滴水不漏的讲出来,我在家里不断的用个标签记录分析这个作品终究也没有贯穿它。 但博尔赫斯自己是非常清楚的,那些研究者也非常清楚,但是我自己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东西,但是《南方》这个小说恰恰帮助我们完成了一这点,所以我们选择《南方》来这里讨论,也许会给我们今天当下的写作提供另外的可能。 2. 《南方》这个小说故事非常清晰,我们能够非常清楚的用几句话把它讲清楚。小说的开始像记实文学一样,我们今天说他是另外一种想像虚构和叙述,但是《南方》这个小说完全像一个记实文学的开头。在1937年如何如何,主人公的福音派牧师爷爷从德国如何登陆到这里传教,然后他有个孙子就是主人公达尔曼,达尔曼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图书馆的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图书保管员。这个非常简单,但后边开始才是真正的小说,前边我们发现实际上非常纯粹就像记实文学一样,时间、地点、人物都非常清楚。  听课的读者 但注意后边真正小说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开始只是因为他这一天他喜欢《一千零一页》,他顺便走在大街上买了一本《一千零一页》的小说,当他去看《一千零一页》想尽快回到家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电梯上等人比较多,他就顺着楼梯爬上去,这个楼梯灯光比较昏暗,上去的时候因为某一个楼梯的窗子打开了,他一头撞到窗子上,撞在窗子上捂着头回家一看,有一个女人给他开门,说你的额头给撞破了,他一摸额头上是有血迹,故事就这么简单。 有血迹之后他就每天疼每天发烧,就住到医院,一检查发现原来不是窗子把他的头撞破了,原来他是得了败血病,这个败血病不重要,重要是他在医院不管住了多长时间,当他有病以后他一直在想念着在南方,他的爷爷给他留下的一个庄园。他一直说他的爷爷给他留下这个院子,但是他种种原因从来没有回去过,当知道自己败血病的时候,和我们一样他想到了叶落归根,想到了回家去。 于是当他的病变轻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搭火车回到他的家乡去了。全部的故事就这样,他到达家乡那个小站,这个小站因为在黄昏时还不能随时到家,他就去租一辆马车然后到杂货铺里吃一点东西,杂货铺里边特别像我们今天那样,有几个民工,民工在那喝啤酒,喝酒的时候就用小面包块往他身上砸一下,砸一下,砸一下。结果他们就吵起来打起来了,最后他们就说我们到草原上去对打一场,看谁能打过谁,他就和那个民工去了,小说就写了这样个故事。 我想这个故事讲起来毫无意义,谁都能看得清楚。但是我们去分析这个小说的时候,恰恰是这个在我们看来既不写跌宕起伏,也不塑造多么丰富的人物,更不会写人性生命那些东西的作品,有非常多有趣的地方。我们首先看这个小说中的时间问题,我们每天都在讨论博尔赫斯小说的时间,我们发现在这篇小说中间,在小说的开头有非常清晰的时间,完全像记实文学:1937年如何,1871年他的爷爷如何,到1939年他的孙子如何,到了1939年的2月达尔曼买了这个《一千零一页》发生了头撞在窗子上,之后发现败血症之后回家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时间是非常确凿的。 博尔赫斯特别会写小说的,几乎每一篇小说的开头,《交叉小径的花园》、《环形废墟》、《阿莱夫》,以及其他的小说,开头几乎都是时间和地点,言之凿凿,事情非常真实,但在小说的最后,所有他提供的时间一点点不再准确,这是这些小说最奇妙的地方。《南方》里不管前面多准确,说到住医院以后,达尔曼回家以后再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一个时间了,只提供了说某一天几分钟以后,八天以后,什么什么的秋天。  博尔赫斯 当这个人物真要回家的时候,决定回家的时候,出院的时候,小说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准确的时间,全部是模糊的,不确切的,值得怀疑的。其实在这个小说中间隐藏了一个时间的最奇妙的问题,当我们写作的时候我们会把时间写的越来越准确,现实主义也好现代派也好,在时间上是一点不能含糊的。 但博尔赫斯恰恰在最准确的时间之下,写了一些最模糊的时间,比如他写达尔曼住院,住院一段时间以后,这一段到底是多长时间;这中间作家有非常多关于时间的描述,比如说“八天过去了”,但是第一天是从哪里算我们不知道;“手术后的几日里”;然后“早晨七点钟的时候”,这是哪一天的早晨七点钟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发现他的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巨大的真实下边带来一个非常模糊的时间概念,我们说不准达尔曼他住院是哪一天,病好是哪一天,回家是哪一天,是什么季节,我们都无法考证。这些信息对于作者本人来说非常准确,我边上有一棵柳树,我门口有一个大楼,你到底在哪里,我边上有一个电线杆,电线杆是灰色的,水泥电线杆有多高多高都说的非常准确,但是对其他人完全是模糊的,没有参照。 这就是博尔赫斯的非常奇妙的时间,这个小说里也同样是这样一个时间的迷宫,就是说开始的准确就像记实文学一样,但是在后边的时间完全模糊的让你无法对照。这是非常奇妙的。而且我们再去看,为什么我说《交叉小径的花园》无法复数,同样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在《交叉小径的花园》开头讲了《欧洲战争史》在哪一年出版,那一年出版的《欧洲战争史》多少多少页有这么一段记述,那个《欧洲战争史》的出版时间非常准确,但是讲《战争史》里边第二百七十二页讲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时间是没有的,他完全用时间把我们模糊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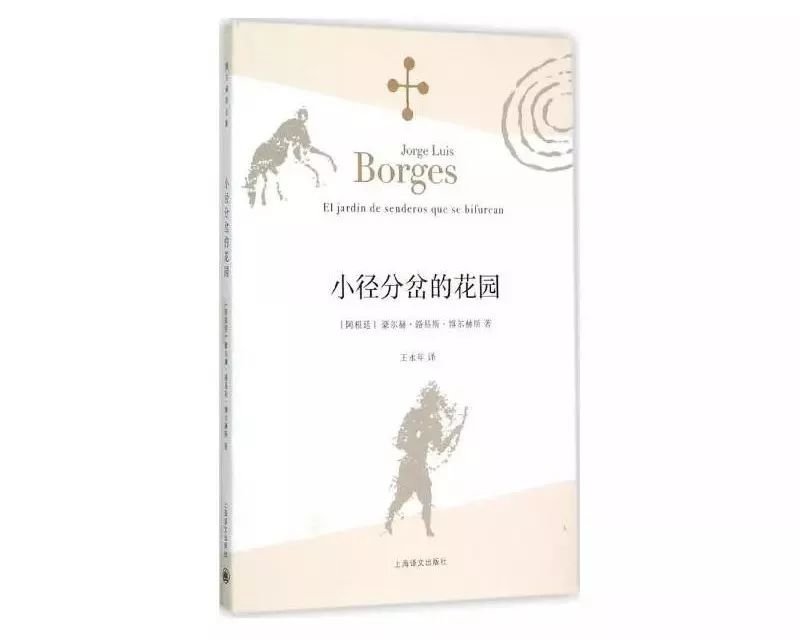 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 每一个小说都有准确的时间,但故事的发生全部是模糊的时间,是无法确定的。我们看他的《环形废墟》,某一天看《一千零一页》的时候在什么地方想起了什么东西,你看《一千零一页》的时间非常准确,但这并不代表这个《环形废墟》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准确的。所以我们说没有人能够像博尔赫斯这样对小说的时间运用的这么奇妙,他的所有时间都是错位的。开头谈的特别准确,但是和这个故事没有关系,开头言之凿凿哪一年哪一年,到了最后其实时间都是模糊的,这是这个小说的时间问题。 3. 我想第二点更加有趣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写小说时永远在谈论人物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一切故事的发展都要根据人物性质,这是因为有了人物才有了这样的故事,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一定没有这样的故事。但《南方》完全不是,那些故事和人物毫无关系,我们刚才讲的达尔曼回家的故事和这个人物的性格毫无关系,这个人物性格到最后我们都无法确定。他只是说这个人物在内心上稍稍有点压抑,我们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压抑。为什么说他这个故事完全不靠人物在推进,那他靠什么?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刚才讲的故事中间,全部都是靠偶然加偶然在推进情节的,没有任何必然。 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之所以不再爱他的丈夫卡列宁,是因为她发现丈夫的耳朵长的特别丑特别大,她从发现耳朵难看以后,对她丈夫一点一点一点不再爱了,小说所有事情都与她的性格发生着紧密的联系,没有那样的性格完全没有这样一部小说。但博尔赫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要写那么长,这也就是个三五千字的小说,为什么他要写那么长。”不管他瞧起瞧不起托尔斯泰,我们发现,博尔赫斯所有的小说,即便是人物故事最清楚的《南方》,故事本身的推进也完全不靠必然,全部靠得是偶然。 第一件事情,买书,是达尔曼因为喜欢《一千零一页》去买的。但是当他乘电梯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等电梯,他没有走,他爬上去了,这一爬上去因为灯光的昏暗,非常偶然的头撞在窗子上了,这是第一个偶然;这个偶然事件发生之后,因为流血不止到医院检查出了败血病,又是一个偶然;败血病完全是治不好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病又迅速好转,先不说他能不能好转,好转以后他就决定回家,回家他在火车上吃饭、看书还打瞌睡做梦这些我们后边去谈。 然后又一个偶然的情节,因为他从来没有回过他家那个老宅,他说那个庄园正好有个小站,他从那下车就可以了,但是故事到这儿,他正在看《一千零一页》的时候,列车服务员来告诉他说,你家那个车站车到那儿不停了,到你家车站前边的站停。为什么这个车站不停了,要到前边那个站停,博尔赫斯也没有讲,这第三个偶然。那么他到这个站又没停,到下边一个站停下来,这是第四个偶然。那么到这站下车就离家远了,远了就要租一辆马车,这都是必然的。 能租的马车很少,马车还没有来他就到杂货铺里坐一坐,吃个东西,吃个菜喝杯酒,然后偶然遇到那些民工,不断的往他头上扔小面包块,这又是一个偶然。之后他问民工你干什么要用面包来砸我,民工说打一架去,到外边练一练,这就来了。本来他是一个图书保管员根本没有能力,又刚刚从医院出院,老板就说他手无寸铁你们都是民工手拿着刀子,凭什么要和他打,偏偏这个时候门口蹲了一个他的同族人老高桥人,老高桥就是当地的土著人,拔出一个刀一下扔给他,我给你一个刀,这个刀一接住那就不能不练了,他对面的是三四个正在喝酒的年轻民工,那也不得不拿出刀去外面到草原上对打一顿,这个小说到此完了。  阎连科 我们发现全部的故事推进不是靠人物,全部是一个偶然接着一个偶然。我们看博尔赫斯的所有经典小说,几乎没有一个以人物性格来推进故事发展,全部是他个人所设置的偶然,还有一点这个偶然也很合理,他有他的逻辑。以《南方》为例,这是他所有小说中故事最清晰的一部小说,最清晰的是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的,而且这个时间地点准确到什么都可以发生,结果和人物关系,人物性格相关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全部是被偶然加到一块的。故事的结果博尔赫斯没有讲,但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那三四个民工和疲弱的败血病患者是什么结局。我们会发现博尔赫斯和我们的写作不一样,他是这样来写故事,来推进故事的。 第三点我们会发现,回头说这个小说究竟写了什么东西?这些都不重要,我觉得不在于他写什么。我们平常要写的,要讲的,全部在他的小说中给省略掉了。我经常说看博尔赫斯的小说,你不仅要看他写了什么,更重要是要看他省略掉什么?他为什么能把小说写的这么短?为什么能把小说写的这么入迷,让所有的作家着迷?我们说他是作家中的作家,为什么会说他是作家中的作家?就是他没有写什么其实更重要,写的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南方》这个小说它到底是省略了什么?这个小说的开头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个女人给达尔曼开了门,这个女人是她的妻子还是她的情人?这个女人就这么一句话从此消失掉,而且我们会觉得他是回家了,家里有个女人非常正常。但是这个女人被她省略掉了,他住院的时候,这个女人也没有陪她去医院,她回家的时候,这个女人也没有陪她回家,一开始我们觉得非常合情合理,但是这个女人从此就消失掉了,完全被他省掉了。这是我们的写作必然会写到的,男亲女爱的东西,永远无法丢掉的东西,完全被他一笔勾销了。这个女人帮他开了一次门,从此这个女人就不存在了,这是一点。 那我们看这个小说,一共4000字,写的最详细是在医院那一段,他在医院如何,醒来如何,打针如何。但是医院里面省掉了最多的,是他怎么去住院的,他住院想了什么?唯一有一点点心理描写的,或者说也不是心理描写,是像中国的白描的,是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前面一句写的是:正在给他打点滴注射,后面一句话:手术之后多长多长时间。前面从来没写手术,博尔赫斯就告诉你已经做完手术了,而且已经开始好转了,博尔赫斯的小说全部呈现的是过程的结果,不呈现过程。 这里边省掉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得的是败血病,唯一能表现这一点的就一句话,当他起死回生时,自己掉下了眼泪。接下来就说,他迅速想回到家里的庄园疗养疗养,去看看那个庄园。所以他该要心理描写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唯一能够符合人物心理的就是,当他知道他起死回生,死里逃生的时候,他掉下了眼泪。这是这个小说中间唯一有人性,有人情,合乎情理的描写。 那么之后我们会发现很重要的一点,全部小说提示是要“回家”,这个小说表达了一些还乡、乡愁,这样一个哲学的、人情的东西。但我们会发现博尔赫斯一点没有写他家的庄园是什么样子,到底你家的房子怎么样?你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庄园是荒废的还是兴旺发达的,什么都没有写。庄园完全成为一个象征,但是这个象征,就象征一个回家的主题,为什么这个象征又没有让我们觉得象征? 博尔赫斯非常非常会写小说,他在小说第二部分开头就写,在达尔曼坐火车准备回家的时候,讲了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边上的小城,他坐了一段马车去那个小城的火车站坐火车的时候,有两句话是:看到大街上的街道,像是庄园的走廊一样。大街上的院落像庄园的小院一样。实质上我们发现,他完全隐藏了那个庄园,这个庄园就在这两句话中,非常清晰。我们从来没觉得,他没有交代是少了什么,但是他在这个地方 |
Copyright © 2001-2024, Wxbkw.Com. Powered by Discuz! X3.5